
■地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疾患:表皮-皮脂腺痣综合症 尽管目前医学飞速发展,各种疾病的致病机理、诊断要点等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但是作为医务工作者经常会遇到“明确诊断的疾病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去帮助患者”的窘境。 ■楼道里,遇到一家三口 “给您开的这药,早晚各两粒儿,饭中或饭后就得马上服用,在这一段治疗时间内,最好吃一些稍微油大的食物,这样药物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年工作时一个普通的门诊日,我反复叮嘱上午最后一个患者用药的注意事项,并帮其预约了下次的门诊,见他认真地点头,心才放下来。等我整理完病历资料,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12点半了,总算可以稍微松口气了,心想着赶紧吃口饭去,不然一会儿就没吃的了。 正当我要穿过走廊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让我放慢了脚步,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一对年轻夫妇正哄着怀里啼哭的孩子。他们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焦虑,于是我上前关心地问道:“孩子怎么了?” “大夫,您快看看孩子吧。我们是外地的,赶过来已经中午了,刚才挂到了下午最后一个号,孩子才三个月大,半个月前开始发病,这两天更严重了……”小孩儿的妈妈焦急地说,声音有些颤抖。我心里一揪,疾步走到旁边一间空诊室门口,招呼他们,“赶紧把孩子抱进来吧!” 我对孩子进行了全面的查体,这是一个女婴,乍一看,和三个月大的小孩儿没有什么差别,小脑袋左右晃着、小嘴不停地吮吸着手指。仔细观察发现,小宝宝的头顶有一小块毛发缺失区,其次在她左耳前方和左颈部位也各有一块皮肤异常,同时左眼眼球也有一块异样的膜状物。检查后,我对孩子整个身体情况已经初步了解。 仔细询问得知,孩子刚出生时,家人就发现了她头顶部和面部的皮肤有些不一样,但也没多管它,以为不会有啥影响。可半个月以前,孩子开始出现面部抽搐,每次持续时间约半分钟-2分钟,每天发作5、6次,后来次数越来越频繁,最多的一天抽20几次。孩子父母意识到情况不妙,带着孩子跑遍了当地医院,做了很多检查,CT提示左侧颞叶蛛网膜发现有囊肿,当地医院就做出了癫痫的诊断结果,并开了一些药物让小孩儿回家治疗。但服药并没有使其病情有所改善,于是孩子父母才下定决心从河南安阳赶到北京求治。 根据刚才的查体结果和孩子父母的描述,我隐隐觉得孩子的病情应该不会是普通的小儿癫痫这么简单,这么小就开始发病,而且症状涉及眼科、内科、皮科等多个学科,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先天性皮肤神经综合症,这只是初步我的诊断,对于刚刚工作一年的我没有十分确切的把握。 正想着,小家伙哭闹的更凶了,原来家长担心做检查需要抽血,从早上就没有给孩子喂奶了。我安慰道:“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你们跑了一天了一定很累了,先吃饭,给小家伙也喂点奶吧,别饿坏了。”已近下午一点,我还没顾上吃饭便匆匆跑回办公室,向有着多年小儿皮肤疾病经验的杨海珍主任寻求帮助。 ■“大牌儿”教授为孩子进行多科会诊 听我介绍完基本情况,杨主任放下没吃完的午饭,也来到诊室给小孩儿做起检查来,最后得出的意见与我的初步判断一致。为了不出偏差,杨主任一边翻开一本厚厚的外文书籍查阅资料,一边让我去带孩子找仍未结束上午门诊的朱学骏教授科内会诊。朱老师是我们科出了名的严谨派,临床经验极其丰富,看过孩子后也同意我们的考虑,但还是建议做皮肤活检、头颅MRI来协助诊断,而这项有创操作对于小家伙来说极易诱发惊厥的再次发作。两位主任一商量,达成一致:请各科的专家会诊给予综合治疗意见比较稳妥。 此时,时间已经将近一点,杨主任继续下午的门诊工作,而办公室的桌上剩下了她才吃了两口的饭菜。对于我们来说,看到她这样也已经是习以为常了。的确如此,很多时候医生出门诊,几乎整整一个上午、下午都没时间去喝一口水。看到两位专家这样的工作精神,作为年轻医师的我既感到无比敬畏、又觉得十分心疼。 我将主任的建议告诉了孩子父母,他们有些迟疑,我明白,他们一方面在担心孩子的病情,另一方面又担心请专家会诊程序复杂,费用不菲。我忙说:“放心吧,我来联系专家。你们安心等我通知,其他的不用考虑了。”这时,孩子的父母感激地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张大夫,这……咋谢谢您呢?”而此刻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已经把眼前的这位年轻医生当做孩子全部的希望了,顿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晚上下了班,想起白天遇到的这一家三口,我赶紧给两个同在北大医院轮转的同学打电话取得联系,希望能请到眼科著名专家潘英姿主任和小儿神经内科著名癫痫专家吴希如主任和遗传专家杨勇主协助诊治,他们可都是业内权威、响当当的大腕啊!听说了孩子的情况后,这些“大牌儿”教授真让我感动,决定第二天就为孩子进行多科会诊。 ■罕见的表皮-皮脂腺痣综合症最小患者 当晚,想着小孩儿可爱的样子,顾不得休息,咬了几口面包,为明天的会诊查起了资料,在医院的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搜索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遇到相似症状的病例就记录下来,以便综合对比。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翻阅了诸多相关文献之后,我发现孩子的病与一种叫“表皮-皮脂腺痣综合症”又称“Schimmelpenning综合症”的疾病极其相似。这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疾病,1968年Solomon首次报道了本病,认为该病为先天性疾病,临床表现可以表现为皮脂腺痣、智力障碍、癫痫发作、眼结膜血管脂肪瘤样增生等。这个孩子的症状和体征极其类似这一综合症的描述,如果成立,这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报道的年龄最小的一例。 第二天,小儿科、皮肤科、眼科专家,甚至还有特需门诊的各专家也到场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足有四十多个。而他们没有收一分钱的会诊费用。我仔细汇报了患儿的疾病过程,临床表现,以及Schimmelpnning综合征的相关资料,经专家反复检查并论证,一致同意了这一诊断,并针对孩子95天龄的情况,研究出一套特殊的治疗方案,初步定为先药物控制病情,等孩子年龄长大一点再择期手术切除颅内病灶。 ■可能是放射源惹祸 拿到了诊断结果和各科专家一起制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后,孩子的父母几个月来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了。我抚摸着孩子嘱咐他的父母,“回去好好配合治疗,按时吃药。”我得知,孩子名叫小凡,父母都是地方医院的职工,小凡的爸爸王哥是一名骨科的医生,平时经常接触放射源,也许这是小凡得病的原因之一。家里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在小凡的大额医疗费用面前仍然显得杯水车薪。 小凡一家人很快就回老家了,也渐渐远离了我的生活,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也总能想起小凡那可爱的小脸。由于这次经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平日里常常保持联络,给他们一丝慰藉,并几次帮他们在京购药寄去。遇到六一儿童节,我也会抽空给孩子寄去一份礼物,虽然并不贵重,但还是想以此鼓励小凡和小凡的父母,给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祝福她健康快乐成长。小凡的父母也在年终岁末时会寄来以小凡署名的贺年片,当然还有小凡的照片,这些我都细心地珍藏着。 时间如白驹过隙,两年过去了,随着小凡一天天长大,癫痫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发作的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药物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微弱,有时候剂量增加一倍以上都无济于事。我也帮忙请示过专家,并转告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让他们去神经外科最具优势的宣武医院看看。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记得那是去年夏天一个值完夜班后的下午,尽管一整晚都在抢救一名危重患者,但此时却没有丝毫的困意,因为小凡来了,我要去看看这个小家伙。从单位出发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和地铁,终于到了宣武医院。刚出站口,就听到有人喊:“张大夫!张大夫!”时隔两年,小凡的爸爸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两双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个瞬间,我看到了王哥眼睛红了。在去病房的路上,王哥详细地给我阐述了小凡这两年来的病情变化、服药情况。我看到他一声不吭、沮丧地低下了头。 仔细询问才知道,入院后小儿神经外科的国内知名专家已经组织了相关会诊,小凡目前状态手术的话风险极大,建议继续内科保守治疗,待时机成熟后,方可择期手术治疗。在那一刻我真的可以体会身为人父的王哥此时的心情。 在那一刻我也真正理解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奈,我正在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倍感自责时,突然发现小凡那双可爱而无奈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看,还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充斥全身,再多安慰的话语,对于一个脆弱的生命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空洞乏味。临走时,我把事先准备好的500元钱和写给小凡的一封信,偷偷地放在她的枕头下面,希望这个不幸的小女孩在这么多关爱人的保护下健康成长。 小凡,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可她所患疾病却让她的人生不再平凡。我作为一个医生站在小凡面前,枉有七尺男儿之身,显得渺小和无奈。医学发展迅猛,可在千变万化的人体机器面前,我们仍常常深感爱莫能助。什么是医生的职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克鲁多的话让我陷入深思,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治愈才会多些、再多些,这也成为我不懈努力的动力,因为有太多的“小凡”在等待我们去治愈,等待我们去帮助、安慰。 ■文/张斌(北京地坛医院皮肤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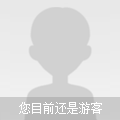
| |
| 上一篇: | 下肢突然无力可能是中风 |
| 下一篇: | 压力面前女性心脏弱于男 |